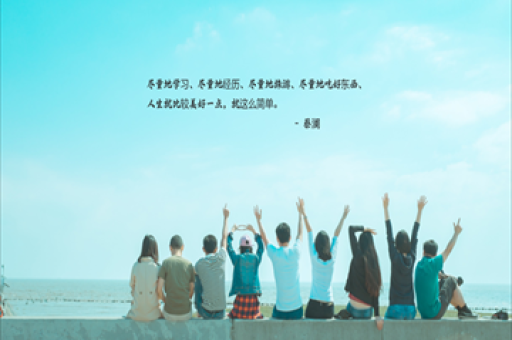老外不爱中国白酒?这个美国人想试试
多年以前,旅居中国的美国人德力·桑德豪斯(Derek Sandhaus)还没有成为白酒研究者,甚至分不清二锅头和汾酒的区别,但他当时就决定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主题是白酒。“我的灵感来自一种看似矛盾的饮料,它在本国备受喜爱,但在国外却不受待见。我错过了什么?我想知道。我们又错过了什么?”
于是,他开了一个博客,去了当地的酒铺,开始写作。2014年出版的Baijiu:The Essential Guide to Chinese Spirits(《白酒:中国烈酒必备指南》)、2019年出版的Drunk in China:Baijiu and the World's Oldest Drinking Culture(《醉在中国:白酒与中国最古老的酒文化》),让他成为白酒专家。在接受外媒采访时,他表示:“没有人在好好努力向西方人介绍这种酒。”
2024年,《醉在中国》推出简体中文版。该书的简介写道:“四川泸州老窖、贵州茅台、桂林三花酒、绍兴黄酒、山西汾酒、河南杜康……在走遍大江南北、品饮各地名酒的同时,他也拜访了当地的酿酒师、考古学家、经销商和资深酒友,在酿酒车间、市井小馆、隐秘酒吧和诗歌故事里发现中国九千年酒饮文化的各个侧面,以及酒中蕴藏着的中国人的精神与情怀。”
德力从一个外来人的视角,呈现了白酒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历史和文化,借此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这个古老又鲜活的国家。
让西方人爱上白酒,是件难事
如同大多数美国人,德力童年时期有关中国的回忆寥寥无几。“仅限于儿童电视节目《大鸟在中国》、跟我的犹太家族去中国饭店聚餐,以及小学美术老师对中国水彩画的喜爱。”
大学毕业后,他在波士顿郊区沃尔瑟姆一边做着一份毫无前途的工作,一边等着女友凯瑟琳毕业。21世纪的头10年,美国从政治到经济等各个方面都跌入让人心惊的低谷,与此同时,大洋彼岸的中国正在创造着一场又一场经济奇迹,媒体将21世纪称为“中国世纪”。
怀揣对这片热土的朦胧期待,德力来到上海——“一座杂乱无序的国际化大都市”。2006年的感恩节,在上海一座高层公寓里,德力*次感受到中国白酒的威力。
那是一瓶二锅头。“这种气味让我完全没有防备,闻起来就像是有人把一包脏污不堪的运动短裤塞进了一桶发酵鱼露里,再加入下水道疏通剂、烂水果和蓝纹臭奶酪,之后又浸泡了好几天。那是一种从地狱深渊里升腾起的味道,你闻到这气味后立刻惊醒,发现自己身在一个连环杀手的地下室里,他正准备拿你找乐子呢。”德力在《醉在中国》中这样形容自己*次闻到白酒时的感受。
这气味让他年轻无知的大脑惊恐万分,而当他品尝一口白酒后,他说:“我的嘴瞬间着起火来,白色的火苗烧灼着我的每一寸舌头、双唇、牙龈和喉咙。那液体烫糊了我的食管,在我的胃里扔进了一块燃烧的煤炭。”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德力都无法接受这种刺激性的酒精饮品。
白酒的高酒精度数与刺鼻味道,劝退了很多像德力这样的外国人。2015年,BuzzFeed发布了一个题为《美国人初尝亚洲酒》的视频。视频中,几位美国人先后挑战印度朗姆酒、韩国清酒、日本麦烧酒、泰国湄公酒等亚洲酒种,顺利过关;53度的中国茅台迎宾酒上场,立刻击溃了他们的味蕾。他们纷纷表示,这种酒“尝起来就像毒药”,“好像我的嘴里正在闹离婚”。
同年,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了一篇题为《用中国白酒调制鸡尾酒是什么滋味》的报道。从文章中,我们可以一窥当时西方人对待中国白酒的态度:“白酒还没开始在酒吧盛行,但在过去一年中,它已经建立了坚实的滩头阵地。纽约、华盛顿、洛杉矶的调酒师以怀疑的态度使用白酒,就像他们当时对待酒精超标的威士忌及梅斯卡尔(Mezcal)等同样强劲的烈酒的态度一样。”
然而,让西方人喝白酒仍是件难事。对于大部分美国人来说,白酒仍然是“尝试过一次的糟糕的中国烈酒”。
10年过去了,外国人对白酒的态度似乎没有多大的变化。在书中,德力写到他的发现:“针对英文大众读者的中国白酒信息少得可怜。更糟糕的是,已有信息大多相互矛盾或有明显的错误之处。”中国白酒想被外国人全然接受,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如果茅台酒喝得足够多,
我们能解决一切问题”
为了让自己喜欢上喝白酒、学会享受白酒,德力尝试了各种方法。朋友蒂姆精确地计算出白酒的味觉阈值——300杯。这一理论试图说明,当一个人喝白酒超过300杯,他对白酒的反应就会从负面变成正面。
就像《醉在中国》原版书名“Drunk in China”希望传达的多重意味,德力想驯服白酒这头猛兽,在这醉人的国度成为一个“醉鬼”。然而,“任何想要描述这种经历的尝试都毫无头绪,白酒的中心问题是,一勺液体转眼间就成了海啸”。
转变发生于他在一个酒局上喝到泸州老窖旗舰级高档白酒的那个瞬间:“酒液带着一股凤梨和杏子的果香撞击着我的舌面,咽下酒液后,混合着白胡椒和甘草香味的尾调弥散开来。口感平滑,滋味丰富,让人为之一振。”德力将之形容为“天启降临”。从此,他无可救药且无可挽回地爱上了白酒。
白酒种类繁多,不同类别白酒的口感差异巨大。德力从四川白酒起步,迈进了中国白酒行业的门槛。此后的数年时间,他遍寻中国各处的白酒——从中国东南部醇美的米酒,到由真菌发酵的贵州白酒、犹如寒冰匕首般的北方白酒,他都亲自去喝了。
白酒甚至让他的身体变得更好了。在一次为期两个月的白酒之旅中,德力喝了大约160杯白酒,以及差不多同样数量的黄酒和米酒。旅程开始之前与结束之后,他分别做了一次体检,化验结果显示,他的肝脏在这次白酒之旅后仍然健康,甚至可以说更健康了。当然,要以此证明烈酒对于身体有正面影响,还为时尚早。在书中,德力分享了自己在研究过程中*一次因为喝烈酒而病倒的经历——不过那次他喝的是瑞典烈酒。
长期以来,西方人对于白酒的看法一直存在隔膜,甚至可以说是偏见。真正好喝的酒一面世,就应该有很多人抢着喝才对;既然没有外国人喝,那它一定是劣质的、恶心的甚至是有毒的——这类针对白酒的怀疑论调,在西方世界普遍存在。
实际上,西方人接触中国白酒的历史,远比我们想象的久远。通过大量搜寻资料,德力了解到,19世纪初,*次被证实的“白酒热”就已经在西方出现——鸦片战争前,停靠在广州特定区域的轮船上的欧洲水手*次尝到了一种叫“三烧”的饮料(经三次蒸馏的米酿白酒,即三蒸酒,也称三熬酒、三花酒)。1878年,在巴黎举办的世界博览会上,中国白酒*次登陆欧洲。1915年,在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来自中国各地的白酒厂展示了它们的产品,有三种白酒夺得大奖章,其中之一是山西高粱汾酒。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 美结束了20多年相互隔绝的历史。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欢迎宴会上,尼克松喝到了茅台酒。美国《生活》杂志记者拍到了尼克松与中国总理周恩来碰杯的画面——此前,尼克松被提醒,不要真的喝下茅台这种烈性酒,只需举起杯来碰一下嘴唇即可。
曾任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则有一句名言:“我觉得,如果茅台酒喝得足够多,我们能解决一切问题。”
杯中酒已斟满,中国白酒“走出去”。外国人从对白酒不屑一顾,到像德力一样痛饮千杯,或许只是时间问题。
中国白酒“走出去”
当德力走上白酒探寻之路时,跨国烈酒企业集团也开始进军中国白酒行业。这些企业普遍乐观地认为,白酒即将快速向海外扩张。然而,据德力的观察,这种雄心并没有实现,这些外国企业低估了进入一个由中国白酒企业控制、高度竞争的市场的难度。
随着近几年中国白酒行业从增量市场演变至存量市场,白酒出海的声量日趋高涨,中国白酒“走出去”已经成为所有白酒企业迫在眉睫的议题。
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酒类进出口商分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白酒共向95个目的地市场出口,出口总额为9.7亿美元,同比增长20.4%;出口量1642万升,同比增长6.3%。
据《中国食品报》报道,中国贸促会研究院院长赵萍表示,2024年前三季度,中国酒类出口额的增速高于同期外贸出口额的增速,这意味着中国酒类在中国品牌出海中已经达到平均水平之上。茅台、五粮液、泸州老窖、水井坊等知名白酒企业也在APEC、达沃斯经济论坛、奥运会等全球主流展会、赛事上频频亮相,扩展其国际影响力。
价格过高和关税问题是白酒出海面临的首要难题。除此之外,要让外国人认识白酒,破除各种对于白酒的偏见和歧视,也需要调酒师、酒类咨询师、白酒企业、经销商等各个环节的共同努力。
“从白酒怀疑论者到白酒的拥趸,最后成为白酒‘传道士’,我想把自己所知的一切分享给世人,让更多的人爱上白酒。”在中国生活并品尝白酒多年,德力决定不再只充当一个旁观者,他与多年前引他入门的泸州老窖合作,推出了面向国际市场的白酒品牌“Ming River”(明江白酒),希望“在四川与世界间建立桥梁,让改变中国的白酒能够影响和改变更多人”。
德力的蜕变,折射的不仅是他在味蕾上的驯服之旅,更是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和对话。白酒这种凝聚着数个世纪文明密码的液体,既是一面映照文化隔阂的镜子,也在无形中架起了一座跨越认知鸿沟的桥梁。在文化相互交融的浪潮中,白酒从来不必征服或者迎合谁,只需静候那一张张懂它、愿意品味它的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