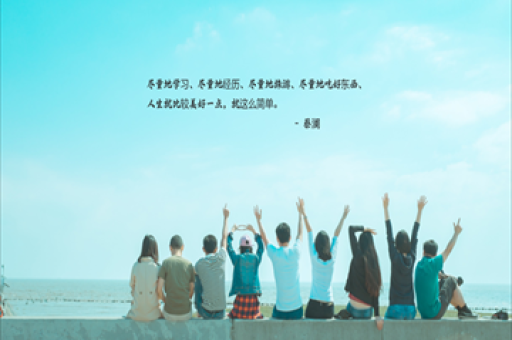当中国biotech开始「上桌」
2025年JPM大会之后,“中国生物科技的崛起”在海外已成为热门话题。
从业内独立撰稿人,到行业媒体Stat、Endpoint,再到《华尔街日报》《经济学人》和CNN 的报道,主流媒体圈不约而同表达了一个观点:中国本土药物创新数量正在急剧增长,与MNC 达成了许多大型交易,给美国的biotech 带去很大的竞争压力。
从崛起到“威胁”,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不同主体的两种视角。
最让美国本土biotech 感到“恐惧”的预测是:“未来,美国市场的许多药物都将是来自中国实验室的分子。”
在地缘政治紧张、美国悬而未决的《生物安全法案》尚未解除对中国生物制药的警报时,有受访的中国从业者在事后表示,其在采访中已试图尽量淡化对中国生物科技成果的“宣传”,“不成为目标可能更好”。
其背后的担忧是,如果最后演化成新药行业的“中国威胁论”,未来,是否可能会影响到初出茅庐的中国创新药企,在国际上的发展?
有从业者表示,至少在业界实际的操作中,“威胁论”并未成为一种主流观点:MNC遵从的是商业逻辑,近年乐于和中国合作的趋势,目前并没有刹车的迹象。
在这位从业者看来,“当年不相信中国生物科技能崛起、和现在对中国创新药资产感受到威胁的,有不少重叠的人群。”这波人的思维方式倾向于二元对立,而不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微观开放式思维。
和大家之前的担忧不一样的是,急需补充管线和新产品的MNC,立足于商业现实:依旧着眼于利用自身的原始创新能力或商业能力和中国的工程化优势,更好更快地做出新药。
-01-
“医药界的中国deepseek时刻已经发生”
“我们正进入一个所有令人兴奋的新疗法都来自中国的时代吗?”这是医疗深度报道媒体Stat;文章的副标题。
去年,美国MNC达成的大型授权交易中有近三分之一是与中国公司达成的。美国业界的结论是,中国本土药物创新数量正在急剧增长,而且不限于仿制或是快速跟随,而是有真正的原始创新。
中国速度令人惊叹。
Endpoint;举出例子:一家有原始创新学术成果的美国公司,从论文发表到真正开始临床试验的五年间,中国已经有公司根据其论文在美国的四个地点开展临床试验。
美国从业者发现,几乎每个领域都有来自中国的竞争对手,“很多时候团队刚开始一个研发项目,回头一看,发现中国已经有六七款针对同一靶点的药物在开发中了”。
这种惊人的速度,以及划算的价格,甚至突破了投资基金们过去所依赖的那一套估值体系——如今在评价美国任何一个资产的价值时,都需要考虑到中国类似资产的价格。
比如,2024年12月,默克以1.12亿美元首付款、高达19亿美元总额的价格获得翰森的一个口服GLP-1资产。这是一个并不算高的价格。消息释出后,拥有类似资产的Viking Therapeutics 股价应声下跌,如今已比当时跌去一半,市值30多亿美元。
实际上类似的例子已发生了不只一次。2023年11月,阿斯利康从诚益生物引进了一个小分子GLP-1,首付款和交易总额都和这次翰森的交易差不多。当时,美国拥有相似管线的Structure Therapeutics 市值超过30亿美元,诚益生物BD成功的消息公示后市值大跌近20%。
中国生物科技产业的崛起给美国biotech 带去的压力已非常明显。引航资本团队成员盛立军观察,特朗普这段时间在针对美国公共卫生系统的改革中,裁掉了2000多名基层研究人员和科学家,这对于美国的新药孵化事业又造成了另一重打击。
盛立军认为,在美国biotech迎来一定的低谷之际,中国的基金也可以去投资它们。两边的基金和企业交互合作,更利于各自的发展和资源配置。
多篇美媒的文章提到康方的PD1/VEGF 双抗依沃西。康方并不是一家多大的跨国药企,而是从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biotech,然而依沃西去年秋天在一项头对头三期试验中打败了全球“药王”K药。媒体们以此作为医药领域的“中国deepseek 时刻”;早已到来的证据。
依沃西的价值早已被美国的资本方关注到。亿万富翁鲍勃·达根创建的Summit Therapeutics在两年前已买下该药物的全球权益,Summit也在这个药物的三期数据披露后市值暴涨数十亿美元,跻身美国生物科技行业头部阵营。
美国媒体在文章中还提到了传奇、恒瑞、礼新等药企。其中Stat提到,凭借来自恒瑞的药物,贝恩资本主导成立了两个newco,其中一家很快被GSK收购(链接:十亿美元学费:恒瑞争议BD背后),另一家公司Kailera Therapeutics在去年10月成立,如今已在进行临床试验,“这(速度)在生物技术行业几乎是闻所未闻的”。
“‘若寻求创新突破,’鲍勃·达根近期受访时表示,‘中国显然是必争之地。’”《华尔街日报》在《中国生物制药行业的DeepSeek时刻》一文中结尾这样写。
-02-
主动选择还是被迫“卖身”
中国创新药企的融资困境,是海外认为的中国biotech 与MNC 的合作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医保改革的支付天花板、科创板第五套收紧等因素,使biotech们直接融资难度已经太高,license out几乎是*出路——既可以拿到一笔能活下去的首付款,又能向投资人证明实力,提高得到融资的可能。
十年的发展,使得中国发展新药的基础设施和生态圈搭建完备,无论是靶点开发还是临床试验,速度和成本都要优于海外,积累了大量早期和中后期资产。
一众资产陈列待售,面向MNC的“管线超市”便形成了。
不过这个超市最后能“开摊”多久,还没有人能说得清楚。《经济学人》的文章中提到了旧金山投资者Jimmy Zhang的担忧:如今的许多授权交易都是过去药监改革和融资热潮的产物,如果没有新的投资,中国的创新药储备可能会开始枯竭。
-03-
“效率”可能不会是中国biotech的永恒优势
在与中国的竞争中,从业者Alex Telford 已经指出西方的biotech 要保持优势的两条路径:
*,专注于原始创新项目。这目前仍是西方业界的优势,未来应更多与*大学部门合作、打通患者数据集,以及构建前沿科学平台。
第二,充分利用云计算和AI等技术,赶超中国团队的效率。
多篇文章也提到了中 美的地缘政治力量博弈、特朗普的贸易保护倾向,对于中国生物科技产业发展的冲击。
但他们并不认为这些会成为阻碍中国biotech的重要因素,他们认为,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生物科技产业的发展仍势不可当。
不过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创新药早期资产的交易高峰可能会有所回落。Stat;的报道提到来自中国*的候选药物正在迅速被抢购,并推高了价格,“但这是有限的资产……最终,这种趋势将不得不结束,整个生物制药界将回到真正的创新。”
对中国biotech最严峻的考验是,当竞争对手利用AI这类工具、以及加速临床试验等手段,在效率层面可能缩小差距后;当年融资热潮的成果也总有被消化完的一天。到那时,效率不再,融资孵化新的果实又跟不上,我们的创新药还能剩下什么?
NewCo孵化机构合伙人彭巍表示,一些MNC对于成熟靶点的各种优化与改良已经表示出“审美疲劳”,这部分工作会被中国企业端下来。而存在重大未满足需求、但研发上有一定难度的领域,比如神经退行性疾病、肾病以及一些难治的肿瘤和自身免疫疾病,可能是他们未来更感兴趣的合作方向。
她认为,今年会是一个“变更之年”,出现一些新的基金,老牌基金会悄然布局自己看好的新的适应症和新的机制,全球合作也可能出现创新的模式。
“现有热点正在逐步出清,等到没有很明显的风可以跟的时候,不如回到做药的本质,好好分析临床需求和相关靶点。而中国的biotech 会在这一轮的全球创新中持续扮演重要的角色,加速best-in-class 和first-in-class 药物的研发进程。”彭巍说。
无论如何,如《华尔街日报》报道中所说的,从患者角度看,全球竞争加剧是利好消息,“癌症患者可能并不在意药物研发地,关键是疗效。”
-04-
可以不只是“新药发源地”吗?
西方媒体在乎未来美国的新药分子是否都会来自中国。而以一种本土视角来看,中国创新药的头部阵营已初步搭建:
百济早以国际化的基因、实力强劲的研发到销售的全链条,跻身世界医药的主流生态圈;
本土生长起来的恒瑞,正以上百条管线尽心经营着一个管线“小超市”,开发的newco BD 模式引领国内行业。
而在以上两个“老大哥”之外,传奇是biotech “借船出海”的典范;
康方的PD1/VEGF 双抗在国际多中心的头对头三期试验中击败K药,成为本次“中国biotech崛起论”的焦点;
百利天恒、科伦博泰等药企抓住了ADC红利,做出了总额近百亿的天价交易;
君实、信达、亚盛等已在国内走通了全链条的biotech,试图向海外走去。
此外,国内传统药企,甚至是国企也对创新药业务有颇多涉足。只是投入不见少,产出还不见多,“医药创新成果多见于小而新的biotech”这一定律,似乎还没有被打破。
西方媒体报道的这一次“崛起”并不会是中国biotech 的终点。照此发展下去,国内创新药企可能会出现两种分化的路线:
*,如西方媒体所言,成为美国新药分子的“发源地”,源源不断地为MNC 贡献早期资产,以融资、上市和合作的BD 款为生,而这也是作为一家biotech 的传统使命。
第二,更多“百济”出现,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作为新药“发源地”而崛起,而是出现一批真正有实力的跨国药企。
这不仅需要创新药企有做全球多中心临床试验的实力,还要有在美国独立搭建商业化团队的能力,真正向一家biopharma 进阶。
难度虽大,但借与MNC 伙伴的合作,共建商业化团队,目前可见有这种潜力的公司是康方、和黄、科伦博泰等。
从这个角度看去,如何从某种历史的“工厂模式”中跳脱出来,亦不满足于只将创新管线授权出去,而要突破本土环境的限制,设法做出属于我们自己的创新大药——恒瑞发展历程的缩影,也许再次折射了中国创新药需要面临的挑战。